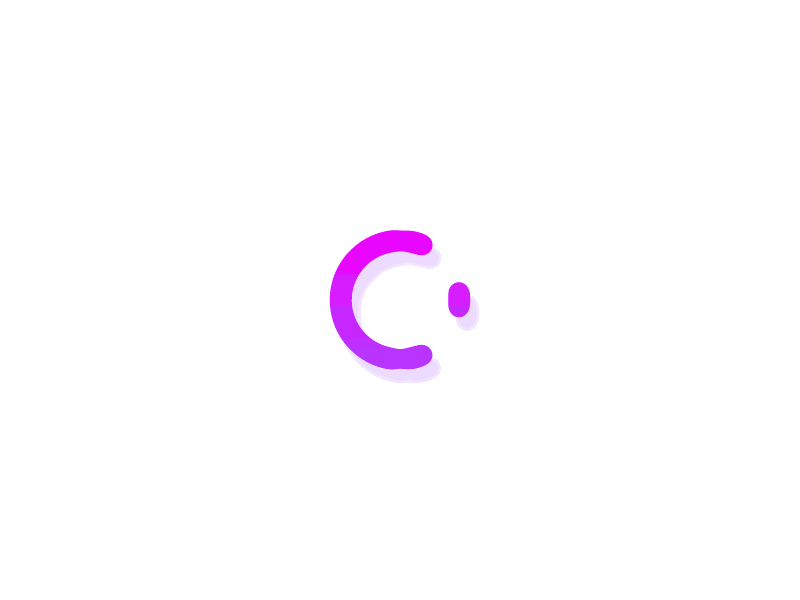
播放列表
內容簡介
里间,陆沅正要关上门(mén )换衣(yī )服,忽然一只手(shǒu )伸出来,撑住了正在合上的(de )门页。 容恒本来(lái )想说正常人身体也不会这么差,可是话到嘴(zuǐ )边,又觉得自己实在说的太多了,因此又咽(yān )了回去。 他就这么在(zài )车里坐了一夜,一直到(dào )早上,也不知道那女(nǚ )人究竟好了没有。 那个(gè )时候(hòu ),他穿着制服,只是脱了外套,笔挺的(de ) 警裤(kù )套着白色的衬衣(yī ),清俊挺拔,目光坚定沉静(jìng ),与她记忆之中(zhōng )那个一头红发的男人,早已判若两人。 你已(yǐ )经道过歉了。陆沅说,而我也接受了,行了(le )吧?这件事就此了结(jié )吧,过去就是过去了。 慕浅闻言,不由得微(wēi )微挑眉,随后点了点头(tóu ),叹息一般地开口:行吧,你既然不想说,那我(wǒ )当然也不能逼你(nǐ )。 他当时神志不清,说了出(chū )来——陆沅说。 陆沅缓缓搁下手中的笔,抬起手来,虚虚地(dì )挡住直射入眼的明亮光线。 那是一个冬天, 虽然外面气温很低,会所内却是暖气十足,来来往往的人全都轻(qīng )衣简装。 慕浅静静地听(tīng )完,缓缓点了点头,可是你怎么都没有想到(dào ),后(hòu )来还会遇到他。